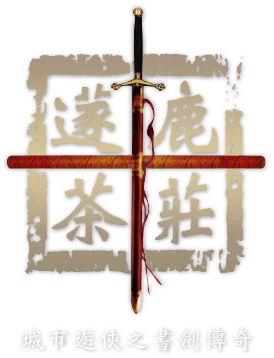《伏蟬留香記》
──阿里山霧裡初相逢,一盞茶,兩段香,一緣長。
阿里山深處,有間小小的茶莊,隱在雲霧與杉林之間,山路曲折,行人稀少,若非迷路,大抵是尋茶而來。
那年夏末,一名年輕女子逆著山風而上,身背茶樣,步履分明。
她叫葉小祐,山下茶農之女,自小在茶園中長大,卻因資質聰穎,後赴城中研習農藝與香氣分析。她識得蟲口的輕痕,懂得香氣的分子結構,也知曉白毫烏龍製程中「等蟲來咬」的不確定性。
這回她返鄉,為的是重整家業,重做祖傳的一款「白毫烏龍」,俗稱「膨風茶」,又名「東方美人」。
那茶極難,製程非難,難在天時地利人不和。非得夏季濕熱,蟬來多、蟲咬多,才能造出那傳說中「蜜韻熟果香」。
但這回她上山,是為試焙。她心知山上有一茶莊名「蓫鹿」,年輕莊主喜讀書、好焙火、愛問茶理,不善市儈,名聲倒是純正。只是……也年輕,聽說還在學。
「年輕也不打緊,能喝得懂茶就好。」她自語。
那日,她踏進蓫鹿莊時,莊主正蹲在焙間檢查焙籠底火,灰燼燙得他眉頭緊鎖。她叫了一聲:「莊主?」
他抬起頭,滿臉灰,但眼神清亮:「有事?」
她笑:「帶茶來試,想借焙房火氣看樣,您這裡方便嗎?」
莊主接過茶葉,搓一搓,聞了聞,抬頭說:「這葉底……被蟬咬過?」
「是啊,小綠葉蟬。」她答。
他沉吟片刻:「蜜香……白毫……東方美人那路子?」
「沿用那個製法,但這不是你想像的膨風茶,我們家的不說故事,只說天氣。」
莊主笑出聲:「我喜歡這句。」
兩人就這樣結識了。
往後幾日,葉小祐常上山送樣,莊主則焙茶請她品評。茶湯漸熱,人情漸溫。
他問她焙茶是否怕火,她答:「不怕,我是山下人,曬得多,火氣大。」
她問他識不識蟲痕,他說:「不識,但我聞得出被咬過的葉,有一種不委屈的香。」
她笑:「你焙茶怎麼這麼會說話?」
他回:「學茶嘛,總得讓葉子先講話,人才會懂。」
話說得多了,茶席兩側的距離似也越來越短。有時她送茶,他忘了準水;有時他邀她喝茶,她說天太熱,要等傍晚再來,卻總準時出現。
他曾問:「這種茶要靠蟲咬才香,不覺得太靠天了?」
她道:「那你焙火,不也靠天氣濕度嗎?茶人哪個不看天?」
「也是。不過我更佩服你這種靠蟲的製法。」
「我也佩服你,靠火的。」
兩人相視一笑,火光閃爍,水聲微響,一泡茶香緩緩升起,像話未說完,卻已讓人心動。
幾年之後,山上的焙房仍有煙氣,山下的茶園更見生機。兩人合作無聲,茶香有聲,東方美人的製法,在他們手中成了日常,無需多言。
有人問葉小祐:「你讀了這麼多書,怎麼還甘願留在山上,陪個焙火的傢伙?」
她笑答:「他泡茶的樣子,比城裡任何一場發表會都精彩。」
至於莊主,他焙火時,案頭總放著一包白毫烏龍。茶名未寫,只簡簡單單貼了一張紙條:
「伏蟬留香」。
他說,這是她帶來的茶,也是她留下的名字。
幾年過去,茶園依舊靠天吃飯,焙房仍與火氣為伍。她繼續在山下看蟲看天,他持續在山上看火看香。每年蟬鳴響起時,她便會提著今年的茶樣上山,一壺一壺地試,問他:「今年這一泡,有沒有去年的甜?」
他總答得認真:「甜多了,去年人沒這麼常來。」
來來往往,說是試茶,其實話也試得夠久了。
某天傍晚,焙房中火氣未散,她剛放下茶筒,他忽然問:「這幾年妳泡的茶,總帶點桂花香,妳有加料嗎?」
她挑眉:「哪有。那是氣候,是葉子,是蟬咬得剛好。」
他點點頭,忽又笑道:「我看不是,是人變了。」
她未語,只在焙房的煙霧裡看他一眼。
那日之後,葉小祐搬上了山。
再後來,有茶商來訪,看見她在焙房指著火道:「太旺了,溫一點才出得來蜜味。」又見他一旁點頭如學生。
茶商問:「這位是……?」
他微笑著,替她倒了一盞剛焙好的茶,答得簡單:「我夫人。」
那盞茶香氣馥郁,蜜韻悠長,如同故事本身——經歷過蟲咬、火焙、山路顛簸,才留下那一縷最柔和的甘甜。
有些茶,要等蟬來叮咬才香;
有些人,要喝過幾壺,才知她留得住你。
📚《伏蟬留香記》──記莊主與夫人初識於茶,一緣天成,香留人間。
📚註:東方美人為台灣特有白毫烏龍之一,茶芽須經小綠葉蟬叮咬方能產生蜜香與熟果香,製程極為仰賴自然條件,故得之不易,香氣獨特。